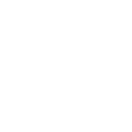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以及对晚清变法的忠告
伊藤博文对话李鸿章:我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趣历史
2014-10-09 10:56:35
如果没有“长毛之乱”,李鸿章这等人物充其量是地方二等官,绝对到不了朝廷大员的位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之臣”是通过“非正当”的渠道仕途高升的,应该具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官场中心之后,也蜕变为噤若寒蝉的动物。可见,还是生存空间与官场环境决定一个官员的素质。
李鸿章、曾国藩们在国内是一流的官员素质水平,然而一旦拿到国外,就根本失去了“优越性”。他们顶多是利益集团的佼佼者,而不会成为信仰集团的精英。所以,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也是无济于事的。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人在接触李鸿章之后,认为中国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俄国人以为李鸿璋代表中国。而在国内,如此素质的官员已经算“杰出”与“优秀”。可见,当时清政府中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是何等垃圾水平。
当李鸿章与袁世凯这样在清政府里“优秀”的官员与世界发达国家官员对比时,且不论西洋,即便是东洋,也不在一个级别。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曾经的对手,忽然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凭的是什么?
国家之道与首相的处世哲学决定了一物降一物。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
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吗?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呢?李鸿章所抱怨的弥漫于中国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旧势力对近代化运动的阻挠破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鸿章又算是哪种进步势力呢?
我们不能拿敌国首脑的谀辞当做“真理”,关于李鸿章,梁启超早有到位的评价——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这种“人杰”,正如启超所称,为“庸众中的杰士”,所谓“庸众中的杰士”,毕竟还是庸才而已。
作为“改革总策划”的李鸿章,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势必被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所淹没。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响亮一记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吗?只不过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罢了。
看伊藤博文当年,明治维新前,反对改革的幕府军何等猖獗,他们打得改革派西乡隆盛大败自杀,日本改革派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乡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继续追随大久保利通改革阵营,反对幕府统治,力主“开国进取”。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彻底性,岂是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吗?
翻看《马关条约》那段历史,必须承认:李鸿章对改革的见识与胆略,比伊藤博文差了一个档次。以李鸿章的胆略,即便放到日本,怎么会比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也要推进彻底改革的伊藤博文干得好呢?
在胜利者面前,必须指出失败者的残缺。享用着胜利者谀辞的失败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开脱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个失败的轮回!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为不同,当然是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所决定的不同“物种”的巨大差距。
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近代政治家,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如此差距,岂不正环环相克,天敌俱现哉?
伊藤博文从思想上,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开明“藩士”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质变。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19世纪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一往无前、不遗余力。
当时世界的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这是近代化国家的根本国家之道。而晚清的国家之道只是被动地换汤不换药,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种国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员,即便是洋务派,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比起资产阶级改革家来,差的不是一丝半毫。
虽然伊藤博文还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识,他大力推行“天皇制的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毕竟推动了日本的质变——一个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而裱糊匠李鸿章所致力的“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晚清,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胆识。思想的局限,使李鸿章不停做出荒唐之事。
关于李鸿章的生存哲学与外交作为,常使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某人卖母,语买者曰:此吾母也,汝当善待之。
呜呼!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可乎?
李鸿章诚如卖母之人,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算是哪等的人杰呢?
封建官僚体制下的首相哲学,除了固步自封的固态哲学,剩下的只能是亦步亦趋的家犬哲学。主人永远是对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与真理观。彼时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李鸿章为国事可跟她据理力争过一次吗?她让他打就打,让他卖国就卖国。因为他深知,只有这个主子能确保他的官位。
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而没落的王朝,国家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
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务型奴才”,即“大勤务兵”,并不指望谁替她定国安邦。
李鸿章的出现,恰恰满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国家需求。
庸相李鸿章,最懂慈禧太后的心思,做好“大勤务兵”,并在“裱糊方面”的功夫一流。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苟延残喘功夫一流,故最得太后之心。太后需要他与友邦周旋,忍国家之辱,负权贵之重。
清朝是中国官员最奴化的时代,大员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称。朝廷用人讲究的是“我的奴才”。奴才所做的一切是为主子服务,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都可以置之度外。就如这直隶总督李鸿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一茬接着一茬,你以为他是“为国分忧”,其实他不过是“为太后分忧”,他就是“唯老佛爷马首是瞻”的一奴才,其升官路数跟大太监李莲英没有本质不同。
伯乐的眼界与需要,决定了所相之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是少谋寡断的,或者英年有为的,那么她或许需要真正的人才为她开天辟地,但事实上,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既不有为,也不少谋寡断,而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然后才是才。先奴后才者,不庸岂不拙拙怪事?!
一个庸奴,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敬业”,或肝脑涂地,或殚精竭虑,也注定成为不了“伟大首相”。
而真正的杰出首相,一般少“乖乖”多“独断”,这正是李最忌惮的,也是庸才与英才的又一大界限。李鸿章为了“拼命做官”可以放弃一切尊严,他给慈禧太后提供服务,一切按主子意志行事,为主子忍辱分忧,却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位以“拼命做官”为毕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用已经满足的权力去冒“变法图强”的风险。做事为了做官,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这就是李鸿章的“官本哲学”。
官僚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做事是为了做官,后者做官则是为了做事。前者没有精神追求,而后者则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伊藤之所以成为李的天敌,除了客观政治处境的不同,根本差异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封建官僚的距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一个老成的封建官僚去对付一个杰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乃圏中老狼与草原头狼的博弈,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草原狼战胜羊圈狼是必然结局。
伊藤博文的警告:中国改革不可急躁
2015年02月09日11:26 中国经营报
http://history.sina.com.cn/bk/jds/2015-02-09/1126116450.shtml
不久,大清帝国果然如伊藤博文预料的,在两年左右就轰然而倒,但所谓的“宪政”乃至“共和”,并没有真正地出现,中国继续在“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夹缝中摇摆……
作者:雪珥
中国改革应该如何把握节奏?
对此,日本著名政治家、“明治维新”的设计师兼工程师之一伊藤博文有过多次阐述,不乏振聋发聩之处。
“中国又睡觉矣”
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日本支持的“开化党”,劫持国王,试图驱逐宗主国中国。应朝鲜政府之请率兵驻扎汉城的袁世凯等,果断出击,粉碎政变,令日本的阴谋难以得逞。
事后,日本遣伊藤博文前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中日条约。这是李鸿章与伊藤初次见面。
对于比自己年轻18岁的伊藤,李鸿章相当欣赏,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报告指出:“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根据10年后他们的回忆,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
归国后,伊藤也对其国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改革。首先,他肯定中国的改革在短期内一定见效,“三年后中国必强”,但是,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日本之所以不必担心中国,主要因为中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
他安慰那些被中国的崛起态势、尤其是袁世凯在朝鲜的亮剑精神震惊的日本人,中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即中法在越南发生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至此,伊藤提出了其对中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中国必须改,但中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要“睡觉”;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渐进。这两点,贯穿了他此后的一系列论说中。
基于如此判断,他认为,当下日本要韬光养晦,暂避中国的锋芒与锐气。“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即中俄围绕伊犁问题的冲突),始设电线(即电报);自法之役,始设海军”。只要避开中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便是中国的那些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
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此年(1884年)年末,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两年后(1886年),到访长崎的中国北洋海军,与当地警民发生流血冲突,北洋海军有多人受伤,史称“长崎事件”。
对于“长崎事件”,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领事波多野,明确表示:“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被日本解释为中国的武力恐吓。
日本著名间谍曾根俊虎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附上了一张中国报纸,报纸社论要求借此机会收复琉球。
双方围绕事件的责任认定等,都十分强硬,谈判毫无进展。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这就意味着,连一向温和的外交官,也认为只有动武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随即宣布停止谈判,之前所议悉数作废。这一强硬立场,令日方大惊失色,多次要求继续谈判,但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日本高层立即紧急会议,由明治天皇亲自主持,虽无即时决议,态度却开始放软。到了次年,在德、法、英等调停下,日本退让。
“长崎事件”成为中国在近代历史中第一次“以威压人”的胜利。但这次胜利,加深了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的蔑视,虚骄盈庭,导致北洋舰队多年停滞不前,正如伊藤所盼望的“又睡觉矣”。
而日本则因深受刺激,根本就不“睡觉”,开始奋起直追。长崎事件完毕后一个月,明治天皇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从天皇开始,全民勒紧裤腰带,建设海军。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长崎事件”之后8年(1894年),韬光养晦的伊藤博文和日本,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就是改变了中日国运乃至世界历史的甲午战争。
“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在下关(马关),与伊藤博文第二次见面。这两位分别主导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谈及了两国的改革。
李鸿章对伊藤说:“亚细亚洲,我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
对于李鸿章打出的同文同种友谊牌,伊藤博文却并不接茬,而是直接谈及最为关键的改革话题:“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
马关谈判之中,李鸿章与伊藤唇枪舌战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鸿章曾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道:“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是个性非常张扬的政治家,甚至有诗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一点都不掩饰。这样的个性,如果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恐不能服官也”还真是实话,也可算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治弱国如修坏室”
甲午之后,中日两国进入了为期近十年的蜜月期。
伊藤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戊戌变法期间,中国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
这一年9月开始,伊藤以私人身份“漫游”中国。此时因为日本国内政争,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系出无聊”,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
就在伊藤博文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
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正在现场的伊藤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有伊藤支持,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后,伊藤又应英国公使的要求,亲自前往李鸿章宅邸,为已经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此人虽由李一手栽培,但后来自以为圣眷优厚,对李颇有切割之意。李明确表示,如无伊藤的情面,他将不会对张施以援手,险成“戊戌七君子”的张最后被改判发配新疆。
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
酒宴上,两人谈及刚刚发生的政变,伊藤告诉李鸿章,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
“三五喜事之徒”的考语,代表了相当大一群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观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
伊藤到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装饰了黄鹤楼,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伊藤在武昌访问仅仅只有两天,当地的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至少约合1520万元人民币),伊藤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继续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两个论点:一是中国改革必须要有“非常英迈”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
“中国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戊戌风云之后,中国改革的脚步并未停止。次年,中央派出二品大员刘学询率团出访日本,对外公开的使命是考察商务,而实际上还肩负着与日本缔结秘密同盟的使命——这是中日两国“兴亚主义”者们多年来致力推动的。
刘学询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几乎遍访日本政、经两界的所有大腕级人物。根据刘学询日后公开出版的《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可以看出,这一连串密集的会见中,中国人主要谈论的是友谊、睦邻,而日本人更为关心的是利益,并且这种利益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改革上。
这次出访,刘学询与伊藤博文有两次会谈,第一次会谈时间居然长达4小时15分钟。
对于这次会谈,刘学询晚年在接受国民党党史人员访谈时回忆道:“伊藤认为中国如果不改革自强,瓜分及崩溃就会迫在眉睫,但是,中国军队外强中干,无法对敌作战;而中国人口的资源虽远超日本,其税收却不如日本,其中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纳税并非出于自愿。”
刘学询也回应说,中国改革的失败,在于改革者的草率浅薄、敷衍塞责,而不是极端守旧派的抵制,康梁等人纯粹是打着改革旗帜的夺权者和政治投机者而已。
对于刘学询的这种观点,伊藤博文是接受的。
“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1905年,中国决心进行史上最大力度的政改——推行君主立宪,先派出了两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欧美日各国考察政治。
以载泽为团长的考察团,负责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
对于中国的政改,日本一直相当关注。早在考察团成行之前,日本报界就开始鼓吹“日清同化”,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导引中国”,推动中国按照日本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大清国派团出国考察宪政,日本舆论普遍比较欣赏。
的确,中国立宪运动的勃兴,本身就是受刺激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很多人眼中,中国立宪的最好样板就是日本——尽管中央还希望通过全面考察进行不同模式的对比。驻日公使杨枢在奏请立宪变法时,就提出:“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广泛的海外考察后,大清国果然选择了日本作为政改的榜样。
载泽考察团在日本总共28天,行程安排得十分丰富,与其说这是考察,不如说更像一次集体“游学”。除了参观工厂、学校、银行等之外,考察团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聆听日本宪政专家的讲课。
“第一课”安排在正月初三(1月27日),“老师”则是日本额法学博士穗积八束。穗积八束的讲授,重点在于日本宪法体系中的皇权的主体地位。而次日的第二课,讲师就是伊藤博文,主题则是“变法自强当以立宪为纲领”。
在这堂课上,伊藤博文向载泽赠送其所著的《皇室典范义解》与《宪法义解》。载泽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伊藤回答说:“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载泽接着问:“立宪当以法何国为宜?”伊藤说:“各国宪政有二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载泽又问:“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伊藤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
伊藤博文再三强调了稳妥推进的重要性:“政府必宣布一定之主意,一国方有所率从。若漫无秩序,朝令夕更,非徒无益,反失故步。”
伊藤告诉他的中国学生们,其实,立宪与专制的最大区别,只在于法律必经议会协修,而非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
日本的见闻,令载泽等如获至宝。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向中央提交了《日本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在这篇报告中,载泽等提出:
“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自维新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载泽他们能看到“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敏锐的。而“不耻效人,不轻舍己”八个字,的确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精当总结。
“慎重与调和”
1909年春夏之交,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临行前去拜访伊藤。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
伊藤博文告诉窦纳乐,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而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显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与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次会见中,伊藤博文告诉英国人,中国按照目前的改革节奏,一定会失控,三年之内将爆发革命。果然,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四个月(1912年2月),宣统皇帝宣布逊位。
对于伊藤的预测,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这些会见情况都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做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到访中国。1909年10月23日,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谈话开始,伊藤博文自陈:“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如此动听的说法,当时在中国已经没多少人会相信了。日本正全力攫取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最为危险的敌人。
随后,伊藤就中国改革与中日和平的关系,阐述道:中国要自强,目前就该韬光养晦,“趁此和平之时修明政事,要紧着手者一在财力,二在兵力”,但是,改革绝对不可以走过场,“练兵非铺张门面,财政非空言清理所能济事”,只有兵精粮足,才能稳固根本,“中国稳固,东亚和平方可永保”。他坦承,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都取决于中国“内政及国基”。
至于锡良等希望的日本能“持平”对待中国,伊藤博文一口回绝,他坦率说道:“若说到日本人民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
自然,伊藤博文的谈话充满了外交辞令与自我辩护,但也的确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华矛盾心结: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共同对抗西方,另一方面,他们难以等待“腐朽而没落”的清政府自我觉醒、自我拯救,必须先下手为强,乃至凭借武力入主中原。
对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政改,伊藤提出:“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伊藤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这次谈话成为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土耳其和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伊藤对于中国改革的看法,并不孤独。
1909年8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莱齐向华盛顿发出警告:中国过快的政治改革,将可能失控,“土耳其和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这位外交官兼汉学家写道:“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的确,很有可能他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相信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但对于中国引入代议制的不安,不仅限于保守派,相反,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
就在费莱齐发出警报后一年(1910年9月),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会见湖广总督瑞徵,谈到提前召开国会一事。瑞徵对于立宪派速开国会的要求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国会议员来源的各省咨议局只是被一些“海归”及文化人充斥,此时召开国会,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名利场而已。嘉乐恒对此深表赞同,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建议应首先改善国会的人员组成。
美国总统塔夫脱在接见中国特使梁敦彦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在推进政治改革中,实行有限民主是合理和明智的。他以自己在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经历,认为过快的民主进程将只能带来混乱与失控。至于梁敦彦担心美国可能会支持那些激进的立宪派,塔夫脱表态:“就美国来说,她虽然关心民选政府的普及,但不认为普选权应该匆忙扩大,首先应该是有一个人民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础。”
与日本、美国的相对含蓄不同,同样关注着大清改革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接见1909年先后到访的大清高级军事代表团时,毫不隐晦地建议:无论改革如何发展,大清的中央核心必须牢牢地将枪杆子抓在手里,这是维持安定团结的关键因素。数年前,大清国领导核心、摄政王载沣访问德国时,威廉二世也对这位年轻的中国接班人,提出了同样的、更为具体的建议。
无论列强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关切都点中了大清改革的软肋:改革、尤其政改,正在成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得心应手的工具。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不仅没有凝聚,相反更加涣散。以民主为导向的宪政,被彻底走样为政治帮派之间的火拼,无数小的专制小团体、党派纷纷冒头,一边用宪政为掩护,从强者碗里分羹,另一边也在内部全套照搬专制的作风,关起门来过过“小皇上”的瘾,并日思夜想“彼可取而代之”。
1911年,加大了油门的政改,催生了中国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国内多数政治派系十分失望,随即指责政府“伪改革”“弥缝主义”,但美国外交官依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充满希望的人会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但没有理由怀疑皇帝和许多爱国官员要求改革的愿望是真诚的,并且一些改进措施也将随之而来。至少,我们可以希望目前所发动的这场变革将被证明是一场使中国沿着世界最先进国家方向迈进的改革运动的起点”。
不久,大清帝国果然如伊藤博文预料的,在两年左右就轰然而倒,但所谓的“宪政”乃至“共和”,并没有真正地出现,中国继续在“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夹缝中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