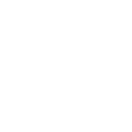章太炎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制度设计,有一套独特看法,其基本特点是将中国传统体制与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实行“法治”。
章太炎认为,在政治制度方面不能盲目效仿他国,也不必执著于民主、专制、立宪之类的概念,而是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中国自己的新路来。他说,君主立宪制度起于英国,民主立宪制度起于法、美,中国应创出第三种体制来,决不能强行“不可行之术”。他说:“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这些概念只能区分政体的“高下”,而不能区分“政事美恶”,“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中国能够从西方共和制度中吸取的,就在于“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这两点,而不是要全盘效仿法国和美国的制度。他否定代议制和联邦制,说“议院之权过高,则受贿鬻言,莫可禁制;联邦之形既建,故布政施法,多不整齐”。美国存在“臧吏遍于市朝,土豪恣其兼并”的“弊政”;法国在这方面稍好,但其根本错误在于“一意主自由”,其结果是“民德已媮,习俗淫靡,莠言不塞,奇邪莫制,在位者无能改革,相与因循,其政虽齐,无救于亡国灭种之兆”。他说,中国如果盲目效仿这两个国家,“则朝夕崩离耳”。
章太炎对秦以后的政治没有全盘否定。他说:“秦、汉以降,政虽专制,非无宪章著于官府,良治善法,足以佐百姓者,亦往往而有。”他认为,单就制度而言,君主专制并没有什么不好,“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也就是说,君主专制可以以避免出现特权阶级,有利于矫正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他说:“人主独贵”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凭个人意志和见解而为所欲为,相反,君主必须依法施政,受法的制约,“以持法为齐”,不能“释法而任神明”。从另一个角度说,君主如果“惑于左右,随于文辩,己之错置方制于人”,也就谈不上“独制”。换言之,“人主独贵”与依法施政是一致的,就是要尽可能避免来自于君主个人主观意志或臣属干预的政治随意性。章太炎认为,自汉、唐以下,“人主独贵”的制度实际上有其名而无其实,原因就在于受到了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他说:汉唐以来的历代王朝,“建国之主,非起于草茅,必拔于搢绅”。“拔于搢绅者”一般来说喜欢凸显自己的高贵,喜欢社会等级分明;“起于草茅者”虽然没有这种观念,但喜欢凸显个人的意志,“不能守绳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有本于商鞅的秦制最好,它一方面搞君主专制,扫荡社会等级,另一方面又能使君主“世守法”,不能独断专行。他认为,秦二世而亡“非法之罪”,原因在于当时六国贵族势力强大,胡亥昏庸。
章太炎认为,对治中国传统政治弊病的根本途径是法治。他说,中国不像印度、西方各国那样存在种姓、阶级制度,官员也不能世袭。官员致仕在籍,其家属如果“暴横乡曲”,有时地方官“能捕治之”;“高赀兼并之家”控制人民命脉的情况“千载未有一二”。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卓绝”之处。在章太炎看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弊病在于“三害”:其一是“官吏贼民”;其二是“宦家武断”,即豪绅横向乡里;其三是“岭南人分宗族大小”,存在社会不平等。要消除中国社会政治的这“三害”,正确的途径是实行法治,即所谓“专以法律为治”。具体做法是:
行政与司法分立;司法官既不由政府任命,也不由人民选举,而“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产生。
他认为,官员不兼司法“则无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选举,则无可阿附以骪其文”。他认为,中国“诚欲求治”,最重要的是靠法家的“综核名实”来约束官吏,“惩创贪墨,纠治奸欺”,要使“民所上于有司者,一丝一粟,有司悉以归之左藏,而监守自盗者必诛,挪移假借者必戮”,这才是“切要可行之政”。总之,要杜绝官吏的贪墨。他说,如果能够这样做,“则立宪无益,而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
章太炎认为,人民的自由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在这一点上他吸取了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观念。
他认为人民应该有革命权,如果政府“猝然外交有失,至于辱国祸民,民得临时诛其主”,人民的这种权利可以使得君主、官员受到制约,“不得自擅”。他认为,要淡化反政权的所谓“谋反之罪”,以使人民“不束缚于上”;要重治背叛国家的“谋叛之罪”。要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民无罪者,不得逮捕”,其犯罪者由法律部门惩治。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凡限制人民这种自由权利者,由法律部门惩治。以上各种措施,都旨在“抑官吏、伸齐民”。政府经费收支,每年要公布;“凡因事加税者,先令地方官各询其民,民可则行之,否则止之”。
章太炎曾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做出过一种设计,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其权力仅限于行政、国防,在外交方面为国家代表。章太炎赞同由全民选举国家元首和批准宪法。他说,这虽然也是一种“多数人决定”的制度,但这种多数是“全体国民”,而不是代议士,因此没有弊病。由于总统之位不是“庸才”可以侥幸猎取,只有那些曾任地方大吏或国务官员,且“功伐”、才略显著者,才有被选举资格,因此,虽然由全国人民选举,也不至于毫无规范,搞得不成样子。
第二,建立独立的监察机制。章太炎认为,通过代议制、选举制来监督政府和官员存在弊病,没有实际效力,他主张建立经考试产生的官员监察机构。
他说:以议会监督政府官吏,会降低行政的效率;以司法官员监督议员,则“过半数以上之议员作奸犯科”,“亦无术以处置之”;依靠政党弹劾来监督制约官员也行不通,因为中国的政党缺乏公心,都是“以爱憎为取舍”。他认为,还是应该实行中国传统的御史制度,“分科分道,各司其事”,才不会出现监督之权牵制、干扰政府行政的弊病。关于监察官员的产生,如果靠选举则会产生与议会选举相同的弊病;如果实行任命制“则由政府爱憎”,两者全都行不通。正确的办法是通过考试选拔,“考试及格,则使之互选;选举已定,则政府加以任命”。这种办法与“近代议员纯出选举,唐宋台谏直由任命”的制度相比,弊病要少得多。监察官员任职须有时限,“给事中以在职六年为限,御史以在职三年为限,无使长久淹滞,以失锋利之气”。
第三,司法、行政、教育分立。司法不隶属于总统,其长官与总统平行,如总统犯罪,由司法部门“逮治罢黜”。教育方面,只有小学和海陆军学校隶属于政府,“其他学校皆独立”,教育行政长官与总统互不统属。
有人认为,司法、学官与总统分立,等于是设“三总统”,会导致“事有稽留”。对此章太炎解释说,这三者“各视其事”,“责有专负,事有专任。辛亥革命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章太炎不再反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但主张“三权”之外,“应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理由是“教育与他之行政,关系甚少,且教育宗旨定后,不宜常变,而任教授者,又须专门学识,故不应随内阁为进退”。而“纠察院自大总统、议院以至齐民,皆能弹劾,故不宜任大总统随意更换”。
第四,由社会精英制定法律。各项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以此来防止法律偏离公正而片面迎合上层或讨好下层的倾向。
第五,关于官员违法犯罪的惩治机制。他主张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总统按照资历任用官员,官员除非由司法部门检出违法犯罪,“总统不得以意降调”。总统与官员“行政有过”,或犯“溺职受赇”等罪,人人可以向司法部门举报,司法部门“征之逮之而治之”。司法官员违法,由其上级司法官员惩治;上级司法官员如果不予惩治,“民得请于学官,集法学者共治之”。
第六,凭资历任用官员。人们通常认为,凭资历任用官员不利于选拔人才,有可能使庸才占据官位,章太炎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政治本来就应该依法运作,而用不着“贤人”去施展去个人才能。而且,由于有“劳者得超除,溺职者受罢黜”的制度,足以保证“材者”不“沈滞”,“下资”者被“泠汰”。他认为,由于特殊人才无法事先发现,所以按资历任用官员就最合理。相反,如果强调靠总统“知人善任”、选拔人才,则被任用者就可能都是一些能说会道的“纵横之士”。原因很简单,由于“年劳可质检,而怀才不可预知”,如果一定要选拔所谓的“人才”,则往往就只是以“言词捷给”这一点作为标准。这种办法,必然会败坏官场的风气,“以笔札唇舌自用者,率多援引声气,更相题榜,嫉人之是,用己之非”;其更为恶劣者则行贿馈遗,“以结人欢,其誉乃日起”。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任用者如果没有私心,就会“误用佞人”;如果有私心,“且假借尚贤之名,为顿置私人地”。章太炎说:停止按资历任用官员,未必就能够“得高材”;而且“高材固不常有”,偶尔漏掉了一二个,也不是什么大损失。但如果不按资历“任意举措”,致使投机钻营者充斥官场,“其失人且百倍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