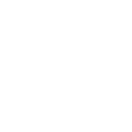刘亮程,一个自然之子,把全部的情感与智慧,倾注在西北一个小小的村庄——黄沙梁。他以独特的视角,诗意的感悟,使单调、平凡、琐屑的乡土生活变得令人向往。他关注着村庄的灵物与灵长,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在追寻乡土生活的同时,也在追寻他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他的乡土情结。
关键词: 刘亮程、 村庄 、乡土情结
不少学者对迟子建、铁凝、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中的乡土情结进行深入的探究,但本人发现刘亮程作为一个“乡土哲学家”,对土地真挚诚恳,对乡村充满热爱,但他的乡土情结却少人关注或者只是模糊地触及这个概念,因而笔者试就《一个人的村庄》展开对刘亮程乡土情结的探究。
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从遥远的西北走来,在当今散文园地中独树一帜。他的文字,像“放到一条透明的小河里淘洗一番,洗得每个字都干干净净,但洗净铅华的文字又有一种厚重。捧在手里掂一掂,每个字都重得好像要脱手。”[1]笔者认为,这种文字的厚重,源自刘亮程倾注其中的挚爱、悲悯、孤独、茫然以及其植根于农业人生的乡土情怀和家园意识。
第二章
“乡土情结”是一种长期郁结于作家内心,对故土和家园无法释怀的乡恋情怀,又熔铸了深刻的文化、历史、哲学的理性思考。
对于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炎黄子孙来说,其乡土情结、家园意识尤其强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刘亮程在村庄黄沙梁生活了二十多年,深深地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其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便不足为奇了。
黄沙梁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记忆,是刘亮程乡土情结的一个成因。在刘亮程人生最初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天山北部沙漠边缘的小村庄,他扛着一把铁锨,游走在黄沙梁,悠闲时东张西望,关心着黄沙梁的灵物与灵长。他和村庄有着不可化解的缘分,“是丰沃而贫困的土地培养了他的感情,他的哲学”[2]——“当他远远地回望这个村子时,他就成了记载村庄历史的活载体,随便触到哪儿,都有一段活生生的故事。”[3]其实,相对于城市来说,生活在贫瘠的黄沙梁,有着巨大的悲剧,因为在乡村里,不仅有精神的惨苦,更有物质的贫乏。小学时,刘亮程要跑到六七公里外的村子上学。“那时他身体赢弱,跑不动,上课老是迟到,于是父亲索性让他休了两年学。”[4]后来,又赶上文革,即使在边疆地区,刘亮程的家庭一样未能幸免灾难。“母亲带着她未成年的五个孩子苦度贫寒的那些年,我们更多接受了自然的温馨和给予。你知道在严寒里柴火烧光的一户人家是怎样贪恋着照进窗口的一缕冬日阳光,又是怎样等一个救星一样等待春天。”[5]
应该说,刘亮程的童年生活非常悲苦不幸,放到别人身上,或许就成了倒霉的坏事,让他的语言充满了不平与怨愤,但“刘亮程把人间的不平,历史的蹂躏统统放在了世界之外,让生命浸漫到每一颗水滴、每一丝微风中……”[6]他说:“一种生活过去后,记忆选择了这些而没有选择那些,这可能是一个人与另一人的根本区别。人确实无法选择生活,却可以选择记忆。”[7]可见,刘亮程乐世的个性内质也是他乡土情结的成因之一。
刘亮程乡土情结还有一个文学背景的影响。21世纪80年代,是诗歌在中华大地上狂欢的年代,而刘亮程也写了十多年的充满乡村情绪的诗歌,并因此而小有成就,告别了贫穷封闭的黄沙梁,从村庄住到城市。同样是时代背景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市场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轴心,同时,物欲高涨、人心浮躁、道德沦丧和人文精神缺乏等,对具有特殊身份和人文内涵的知识分子造成特别巨大的冲击。处于社会转型期,他们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学的功能,并在心灵上更自觉地贴近乡土,回归自然。此时,诗歌成为过去式,刘亮程选择了乡土散文,继续与黄沙梁的牲畜、阳光和风“耳鬓厮磨”。
第三章
黄沙梁的一切都是灵物。在刘亮程看来,“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它们没有走远,永远和人呆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人畜共居的村庄》)
乡土情结很重的刘亮程,用农民的眼光、哲学家的眼光,关注和诉说黄沙梁的牛、驴、狗、马,甚至虫子、蚂蚁。
在乡村,牛和农民通过脚下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一个农民之子、自然之子,刘亮程对牛这种身份与其他生物有所不同的特殊生命的理解才显得更为真切动人。《共同的家》中那一头一岁半的黄母牛多像一个犟脾气的小老头,它先是不肯来,勉强来了又用角抵歪过院墙,用屁股蹭翻过牛槽,还造成了一只白母羊流产。但是,这种“牛脾气”正体现了它对老家的依恋。而之后,全家情感的付出,换来了一头乖牛,让许多素不相识的动物成了亲密一家。《城市牛嗥》是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重头作品。他从“我”偶然路过街心花园,看见冒着热气的牛粪写起,引发了进入城市后的作家内心深处难于割舍的乡土情结,以至于“抓起一把闻一闻”,感觉到“一股熟悉的遥远的乡村的气息扑鼻而来,沁透心肺”。这个典型细节的描写因为有悖于常理,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有矫情作伪的成分,其实恰是十分精到地表达了作家与浸淫已久、同生共体的乡村的血肉联系。[8]当“我”在城市的街上看到一卡车从乡下运来的牛,听到熟悉的一声牛嗥,感觉一车的牛齐刷刷地盯着我,似乎认出“我”的农民身份时,“我”羞愧极了。刘亮程走在城市里,只是听到一声牛嗥,就想到了自己的农民身份。这个乡土作家,心灵里一定固守着对乡村净土的依恋,对乡村灵物的眷恋。
有时,刘亮程也想,“在黄沙梁做一头驴,也是不错的。只要不年纪轻轻就被人宰掉,拉拉车,吃吃草,亢奋时叫两声,平常的时候就沉默,心怀驴胎,想想眼前嘴前的事儿。只要不懒,一辈子也挨不了几鞭。”(《人畜共居的村庄》)刘亮程说,在黄沙梁做一个人,是一件极普通平常的事,牲口比人还通人性,人常常不通畜性。人与畜是“一根缰绳两头的动物,说不上谁牵着谁。(《通驴性的人》)相比之下,人比驴活得艰难。驴坦荡,傲视一切,忘我乃至无我;而人被种种绳索规范着,需要体面,需要风光,需要让别人垂涎。刘亮程厌恶和拒绝这种城市心理,所以他认为做一头驴不错,他渴望他的声音有朝一日可以爆炸出驴鸣,哪怕以沉默十年为代价换得一两句高亢鸣叫也乐意。
在刘亮程看来,黄沙梁的狗迎合着人,黄沙梁的人宽容着狗。他这样写到:“人一睡着,村庄便成了狗的世界,喧嚣一天的人再无话可说,土地和人都乏了。此时狗语大作,狗的声音在夜空飘来荡去,将远远近近的村庄连在一起。那是人之外的另一种声音,飘远、神秘。”(《狗这一辈子》)人的村庄,也是狗的世界;狗的声音,也是人的话语。
对于马,他说:“人和马常常为了同一件事情活一辈子。在长年累月,人马共操劳的活计中,马和人同时衰老了。我时常看到一个老人牵一匹马穿过村庄回到家里……人只知道马帮自己干了一辈子活,却不知道人也帮马操劳了一辈子。只是活到,人可以把一匹老马的肉吃掉,皮子卖掉,马却不能对人这样。”(《逃跑的马》)人吃了马肉,喝了马奶,穿了马皮做的鞋,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会活了一匹马,用马给的体力和激情,干点人的事,撒点人的野和牢骚。
而对于小动物呢?刘亮程羡慕着虫子,因为它们的“生命简洁到只剩下快乐”,他对虫子说:“我认识你们中的谁呢,我将怎样与你们一一握手。”(《与虫共眠》)他自作聪明地帮助蚂蚁搬运干虫,却想不到蚂蚁硬是把干虫又搬回原来的地方;他审视着为搬运粮食而乐此不疲,磨得鲜血淋漓乃至因劳累而死亡的小鼠……
在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人与牛相融,人与驴相通,人与狗相契,人与虫相知……人与动物的关系,让人感到人活着的意义和人存在的悲剧内涵。刘亮程的乡土情结,便在对动物的细腻描写中自然流露。
刘亮程以农民的、诗意的语言诉说着黄沙梁的花草树木。“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摊草惹笑了。”(《对一朵花微笑》)草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对一朵花微笑》)而“我”呢,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看见黄沙梁的树被人砍掉时,他说他已经是那棵树,他会疼痛得叫出声,浑身颤抖,会绝望地看着枝干掉落地上,被人抬上车拉走。(《我的树》)看见麦子黄熟时,他会感慨:“其实人的一生也像庄稼,熟透了也就死了。”(《冯四》)刘亮程与花草的倾心交谈,和树的身份互换,用庄稼比喻人生,恰是他乡土之恋的情感流露,恰是顺理成章的事。
刘亮程的散文意象,总是和乡村有关。他不仅写了动物植物,他还写了其他东西。铁锨是这个世界伸给刘亮程的一只孤手,让他和世界发生了联系。他出门时,一般都扛着铁锨,连进城,也是《扛着铁锨进城》。城里的人有车,有大哥大,他只有铁锨。因为热爱,他从不羞愧,从不自卑。他是这样写门的:“我从屋门出来,走向院门……两道门之间的这段距离,是我一直不愿走完,在心中不让它走完的一段路程。”(《风中的院门》)门是家园的象征,刘亮程在心中不愿走完的路程,正是他在心中不愿离开的乡土。此外,刘亮程还写了泽被人的阳光——“阳光对于人的喂养就像草对于牲畜”(《村东头的人和村洗头的人》);写了猖狂的风——“风呼啸着灌进院子,踢翻地上的筐,撤走绳子上的衣服,一把一把撕垛上的干草往天上扔……”(《我挡住了什么》);写了纠缠的炊烟——它们“细细缕缕地进入每一户人家——从烟囱进入每一口锅底、锅里的饭、锅、每一张嘴”(《炊烟是村庄的根》)……
刘亮程对这些琐屑事物的描写,并不是嫁接的、引进的、杂交培养的,而是在黄沙梁几千年日月光辉中,自然萌动,自然筛选出来的。在这个充满乡土情结的作家眼里,黄沙梁的一切,都是灵物。
第四章
在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他对黄沙梁农民的爱是深沉而不动声色的。
刘亮程抗着一把铁锨四处转悠,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偷窥”着村里的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听他们说话、吵架,谈论收成和女人,偶尔不冷不热地看到我活到这些年龄时会有多大意思。”(《冯四》)
很多年,“我”注意着冯四这个人。没人知道冯四靠什么维持生活,他“经常出门在外,但似乎从没有走出过黄沙梁,按说像他这样无儿无女的人,应该四处漂泊,可他硬是死守着黄沙梁不放,他在依恋什么呢。”(《冯四》)刘亮程对冯四从不离开的疑问,其实表明了他自己的根在黄沙梁,怎么也拔不出来的深扎土地的情感。冯四是个赤手空拳对付了一生的人,他孤单渺小得经常被人遗忘。这个在一个又一个的秋天里,手捂着袖筒,看着人家收成的懒懒散散的农民,在黄沙梁宏大而神秘荒凉的背景里,显得过分地无足轻重,但是,刘亮程仍然关注着他,像看一个神灵一样,带着对生命的虔诚,对乡土的眷恋。
黄沙梁是一个闭塞的小村庄, 黄沙梁的居民是远古的居民。他们卑微、贫乏、无知,他们在村子里留出了道路,但他们走不出黄沙梁,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当村子里来了一个外地的木匠,许多孩子围绕着木匠,看着他在木头上凿眼,把那些木棍锯成一截一截的摆放整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长大了也要当木匠, “过去多少年后,一个村庄里肯定有一大批人把孩提时候的梦想忘得一干二净。”然而,“肯定还会有一个人默无声息地留下来,那一代人最初的生存愿望,被他一个人实现了。尽管这种愿望早已经过时了。”(《木匠》)刘亮程也是那群孩子中的一个,他记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没有跟那个木匠去学艺,而是背着书包去了学堂。刘亮程是幸运的,他因此而可以站在土地的边缘,平视着世世代代生活在黄沙梁的人。现在,他看着这个干得专心又卖力的木匠,猜想着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的命运,做着自己的乡村坚守。
没有居高临下,没有俯视众生的自命不凡,没有讽刺、批判,刘亮程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像个幽灵一样,漂游在黄沙梁里,看着这里的农民。《寒风吹彻》中写到一个老人在冬天被冻死,他感叹到:“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得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刘亮程随时随处感受着村庄里生命的脆弱与伟大,他说:“你白白地放掉他赖以生存的一池救命水,他怒气冲冲地找你拼命时,你笑一笑,赔个不是,送他两跟黄瓜,这件事就摆平了。”胡木像从自己院子里拿东西那样,拿走了“我”买的一跟大木,“我”找上门看了一眼已经做了房梁的木头,一声不吭就回家了,第二天,胡木的两个儿子抬着一根更大的木头送过来,齐刷刷一鞠躬,无言地走了,这事就结束了。刘亮程看着村人的生生死死,喜怒哀乐,从中领略生命给予每一个人的同样的尊严与高贵。
刘亮程用语言解除了贫困、落后、愚昧等等对人的拖累,用博大、沉静、丰富和深厚的感受,给我们展现了黄沙梁农民的“交给时间”的命运,在这种关注小人物的漫长过程中,书写他的乡土情结。
第五章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说:“我全部的学识是对一个村庄的学识。”也许有人说,黄沙梁——这样一个只有冬夜寒风、黄昏炊烟、几条狗、几头牛、几只驴、几个小人物的地方,怎么能让作家的视野开阔呢?但是,“在一个村庄住久了,你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夏粮,而在其他事物身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空气都熟悉了你……”(《住多久才算是家》)现代的许多作家,在不同的地方奔走,试图寻找写作的灵感,与之不同,刘亮程的笔下都只是一个小小村庄,但正因为熟悉这个村庄,理解这个村庄,热爱这个村庄,刘亮程用他浓情的笔墨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圣洁的村庄——黄沙梁。
然而,黄沙梁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乡,“它既是刘亮程的生存之地,更是刘亮程的精神居所。这两者的难以分解就像根和干一样构成一棵参天大树。”[9]刘亮程是一个拾梦者,他沉浸在家园带给他的幸福和满足中。可是,随着农业社会的解体和工业文明的兴起,现代人正一步步丧失精神家园。“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今生今世的证据》)虚无不仅是物质的,更是心灵的。刘亮程惧怕着内心找不到依凭时,郁积内心的空虚感和漂泊感。
他说农村太年轻,农村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老家。刘亮程“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留下这个村庄》),“但在所有的梦中,我都回到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似乎那片土地一直在招呼我们回去,我们成了它永远的劳力,即使走得再远,它也能唤回我们,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地去干那些没干完的活,收拾那个荒芜已久的院子”。(《家园荒芜》)这种乡土情怀体现了作家内心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从黄沙梁到城市,刘亮程多多少少领略到工业文明前行中的残酷性,因而内心潜藏了对失根的茫然与恐惧。在《抗着铁锨进城》的一辑散文中,便可窥见其在城市生活中的无所适从和无能为力——他想一步一步地走进城市,最后彻底地变成城市人,但没想到,家园荒芜的阴影笼罩着他,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生活。这引发了他对黄沙梁的寻找与欲望,对故园的感激与怀念-——黄沙梁便不再是单纯的地名,不再是单纯的故乡,而是灵魂憩息的地方。
刘亮程的根就像父亲那块圈地的界石一样,深埋故土。“那是你家的地,你别想跑掉”,“我没有天堂,只有故乡”。刘亮程了解农民,读懂乡村,在对自然与人类的不慌不忙的描述中,表现了他对土地的虔诚,对家园的虔诚。
刘亮程说:“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当我们老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还乡。叶落归根。”
我衷心希望,住在城市的刘亮程,永远记得遥远的黄沙梁,坚守心中的那一块净土,给高尚的灵魂,一个憩息的家园。
第六章
黄沙梁充满了灵异,刘亮程对其满怀感激和爱。他深情地看着那些琐屑、卑微、纯净又温情无限的乡村事物,就像看着自己的亲人一样,从它们身上,看见人的命运。他心怀悲悯、慈善,看着这里的人在时光中耗着,在天地之上晾着,在虚与实中晃动着。当刘亮程受到城市文明的巨大冲击时,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家园荒芜的恐惧,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在故土黄沙梁上,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样,我们便可以说,刘亮程的乡土情结,也是一种家园意识。就像一个孩子在危险困顿时,总是想到家这个港湾一样。这种依恋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文化积淀,更是作家在对现代文明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时的精神还乡。